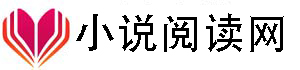60-70(11/29)
东西就很好,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杀了他,未来这么多年的日子里,音乐将会彻底离你远去。”“不!”
祁砚知立刻急切回答道,“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这里是监控死角,我会在他死后清理现场,可以不留下一点儿证……”
“祁砚知!”母亲头一次如此严厉地喝斥他。
“他不值得你赌上后半辈子,你还有很长远很幸福的人生,不应该被这么一个垃圾困在原地。”
“可是母亲,”祁砚知痛苦地问,“我真的很恨他,也很恨跟那个人渣一样控制不住暴力的自己。”
“我是不是真像张阿姨说的那样,因为是杀|人犯的儿子,所以身体自始自终都藏着犯罪的基因?”
“不是这样的,砚知。”母亲仿佛离得很近,又好像隔得很远,她的声音像一双柔软却坚韧的臂膀,在一阵风经过时,温柔地托住了祁砚知慢慢下坠的身体。
“这并不是你的错,砚知,但你不能顺从地接受别人给你安排的命运。”
“你的未来,必须只能由你自己决定。”
母亲的脸庞似乎更模糊了,黯淡无光的阴影里,眼前真实发生的与犯罪无异的暴行,脑海里一闪而过的蝴蝶飞走的画面,无论是音还是形,都渐渐重合在了一起。
“叮”的一下,
掌心血管再次蓬勃跳动的刹那,
母亲的身影彻底消失,清晰摆在面前的是被他自己紧紧箍在墙上,几乎已经陷入濒死状态的简杭宇。
“操……”
简杭宇哪怕被打得这么惨都还在叫嚣,祁砚知揍完他右脸终于得到了短暂的清明。
好笑的是,简杭宇身上疼,祁砚知脑袋疼,如果要问在这种情况下究竟谁疼得更厉害倒也不好说,因为前者看起来青青紫紫遍体鳞伤却至少找得到来源,后者脑袋就像被针扎断了神经,时不时就疼得断片。
不过好在祁砚知最终确定了不能杀人,于是趁着简杭宇差不多还剩最后一口气的关头,动手掰折了他的胳膊。
望着对方慢慢滑落的身体,祁砚知才像刚被人从水里捞出来那样单手抵着墙壁,对着角落竭力呼吸。
耳后的发丝轻飘飘坠到颊边,祁砚知低着头,抽手将它撩到耳后。
今天戴的那只黑色口罩安静地躺在地上,此刻阳光正好,一缕自窗边流入的光辉不偏不倚地停在上面。
祁砚知随意掠去一眼,只觉黑色有些太黯了,跟自己的头发一样,看着颇有几分说不出的压抑。
那染什么颜色呢?
祁砚知缓缓站直了身,抬头望向窗外。
风清树静,万里无云,只有天幕永远存在。
那就它吧,天空的颜色,
跟蝴蝶一样。
胃里时常翻涌的恶心感渐渐消退了不少,祁砚知缓了一会儿吸口气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忽然,身后传来了很微弱的一点脚步声。
如果仔细听的话,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脚步声,因为这其中并没有抬脚的动作,而更像是简单摩擦地面的声响。
可从这点进行分析的话,身后这人应该在这里停留很久了,久到腿部已经开始发麻或是发软,从而不小心弄出了些动静。
“谁?!”
祁砚知侧过身子,用透着一点深蓝的瞳孔朝楼梯口回望。
“别别别,是我。”
很快,一个穿着鹅黄色羽绒服的年轻男人从一面隔在楼梯与平台的墙壁后面走出,或许是站久了腿有点不舒服,那双套在脚上的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