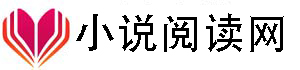40-50(6/38)
我蹲在墙角不敢动,怕暴露也好奇。里面的人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鸟语,但是听起来语气很严肃,大约过了五分钟,我快要在墙根底下睡着了,一声尖利的痛喊穿进我的耳膜,那声音让我想起孤儿院的禁闭室,甚至更加恶劣。我害怕到捂起耳朵,企图封闭自己,但怒吼和惨叫一直没有间断,而且越来越密集。我闭上眼睛把自己缩成一个球,脚趾在那双破烂不堪的鞋里来回抓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手都感到麻木,眼皮因为用力闭紧也开始抽搐。声音好像消失了,我放松了一点,把眼睛睁开,看到了一双很漂亮的棕色皮鞋,鞋头上沾染了一点红色的痕迹。
我抬头,发现沈文兴站就站在我身前,他像一头雄狮一样,眼神里写满了对猎物的渴望。接触他眼睛的一瞬间我忍不住发抖,感官都变得敏感起来,我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直觉告诉我应该跑,但是我的腿软的像面条,身体抖的像筛糠。
他蹲下来,如同一团能把人吞噬的黑影一般压了过来,我又闭上眼,这是我常年面对恐惧的下意识行为,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没有扣住也没有拎起来,就是平稳地、轻轻地放在上面。
“小孩你叫什么?”
沈文兴的声音从我的耳朵里流进来,我的身体定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话,我怕他也杀掉我。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疯狂地摇头,头发在他手心里来回扫,他没有做声,我喊的更凶了,直到身边出现第二个人。
我听到那个人说应该杀了我。
然后我就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多日的舟车劳顿和惊吓已经让我筋疲力尽,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张柔软的床上,身上套着肥大的衬衣,料子滑滑的,四肢没什么力气,但是我感受到了久别的清爽。
我坐了起来四下张望着,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月光透过薄纱淌进来,一直流到床边。我尽量轻地挪到床沿,发现地板上铺了地毯,我的脚踩在上面就像踩在棉花上,那一刻我以为我已经死了,因为他们说天堂是世界上最舒服的地方。
“小孩,你醒了。”
我看见一道光从房间的黑暗处漏出来,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那里。我认得这个声音,我应该还没有死。
他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闻到了一种苦丁茶和香火混合在一起的味道,直到很多年后,我还是清晰的记得这个味道的感觉,沉重、冷静、凄苦,就像沈文兴这个人一样。
“你叫曹燃对吗?”
他蹲下来,直视我的眼睛,月光在他的瞳孔里形成了一个光圈,看起来他很想从我这得到一个答案,但我什么都没回复他。
“我叫沈文兴,你以后叫我文兴哥就行。”沈文兴把手放在我的小腿上,“饿了吗?医生说你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这次我点了点头,并且终于鼓足勇气,对着我的大腿喃喃地叫了一声:“文兴哥。”
·
我在那栋别墅里住了六个月,沈文兴每天早出晚归,我好几次在窗台上看见他从车上下来,衣服上沾着红色不明液体,但是他来找我的时候身上总是那种重复的味道,和雪白的衬衫,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他,比如他和我相遇的那个夜晚被摁在机器旁的男人到底怎么样了,比如他的工作到底是干什么,比如我每天能干什么……这些问题最终都被他那双眼睛堵了回去,我知道我不应该问,也不能问。
后来有一天,沈文兴带回来一对中年男女,他们两个脸上都有点浮肿,衣着看上去也和这里格格不入。我坐在客厅里,摆弄着沈文兴前天给我带回来的变形金刚,他之前让保姆带着我看了那个电影,当然有时候他也会亲